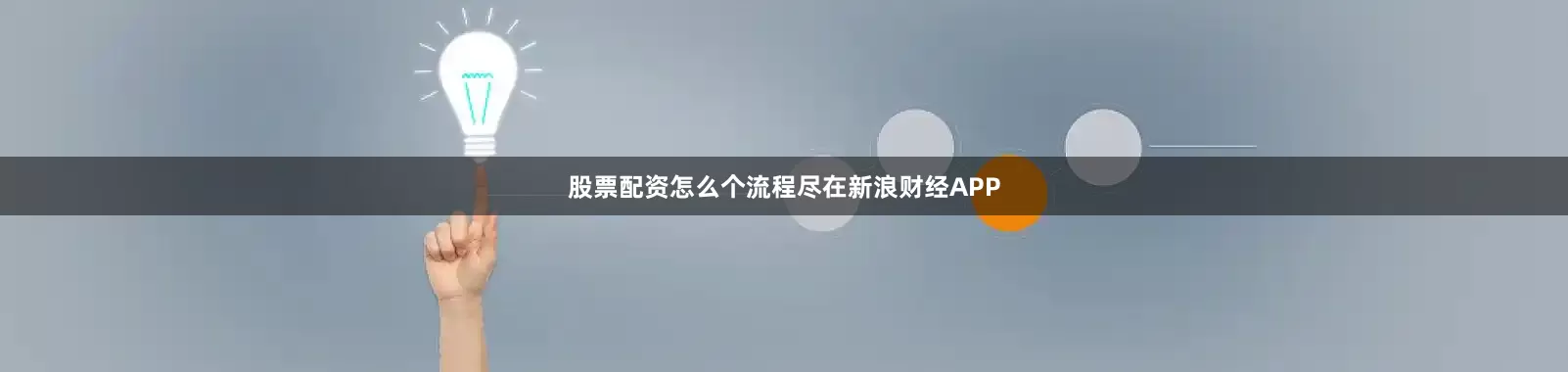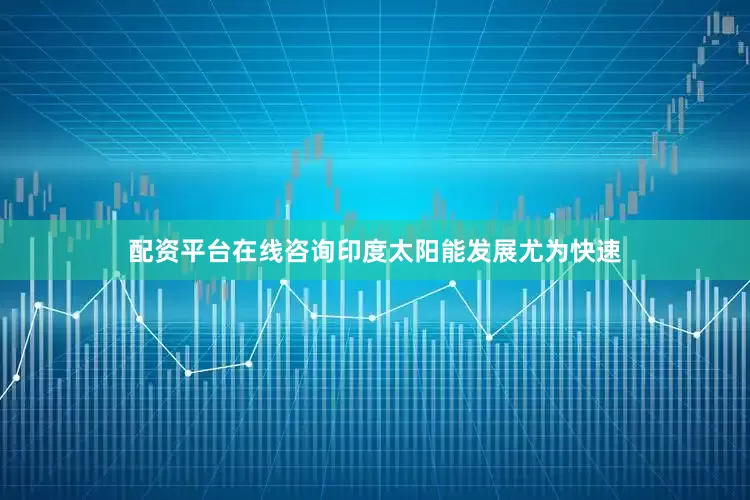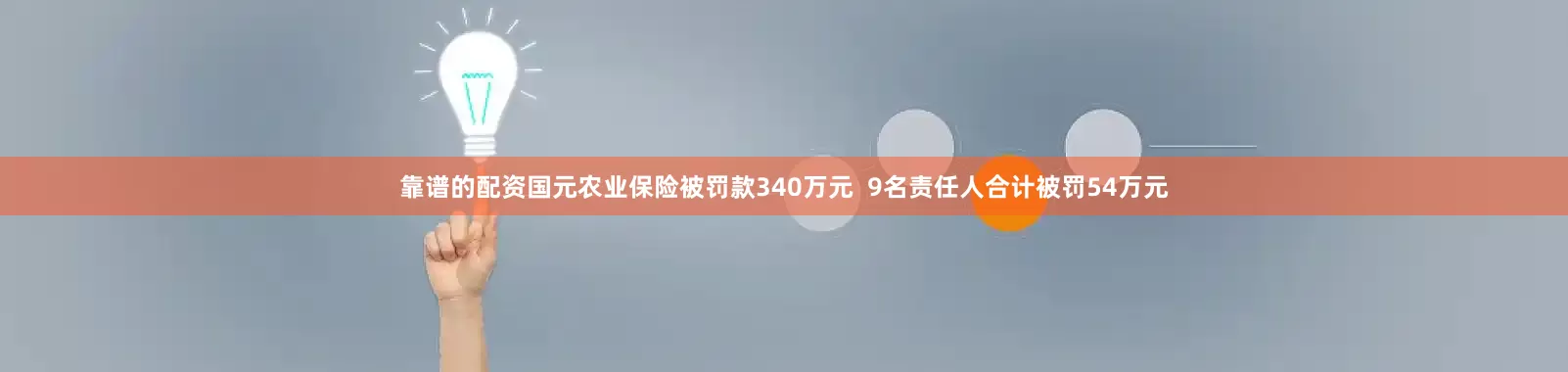好的,我来帮你改写这篇文章,保持段落原意不变,并适当增加细节描述丰富内容。
---
一、士族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表现
之前我们已经谈到,东晋时期的士族精神寄托在庄子的哲学意境中,介绍了他们在寄情于山水、文学艺术上的独特表现,也分析了一些士人在日常行为举止中的具体案例。
不过,士人终究是士人,他们那份洒脱与风度,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是体现在治国理政之上。那么,东晋士族在治国方面的实际表现又是如何呢?
历代对他们的评价总体偏向负面,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:
(1)骄奢自负、能力不足。
(2)缺乏真正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,对百姓多有剥削和残酷。
展开剩余88%(3)对北伐战争的态度多为表面功夫,缺少真诚和实际作为。
总体来说,东晋士人在文学艺术和风雅生活中表现得洒脱俊逸,但在治理国家、平定天下方面,却很难见到同样的风范。
公元339年,王导、庾亮相继去世后,新一代的东晋士人纷纷登上政坛,试图展现他们的才能和气魄。这一时期堪称东晋士族的集体“表演”舞台,但遗憾的是,除了桓温之外,其余人几乎都未能合格。
褚裒面对有利的形势却连连失利,羞愤而自尽;殷浩北伐两次均告失败,谢尚在其中负有重要责任。荀羡、诸葛攸、谢万等人,甚至丢失了桓温两次北伐所取得的成果。
而刘惔、王濛等号称东晋顶级名士,除了躲在幕后发些冷嘲热讽之外,几乎无所作为。
他们的骄纵与无能,在谢万和王徽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,下面详细分析这两人的表现。
---
(1)谢万的日常表现与战场作为
谢万是谢安的弟弟,江南名士,喜欢谈论老庄哲学,似乎颇有“不为外物所动”的风范。
一次在送别支道林的宴会上,他与蔡谟之子争夺座位,被推下椅子,却不露怒色,事后也不追究。
谢万经常摇着扇子,坐着肩舆,评说人物,甚至连他岳父王述也不放在眼里。王述升任扬州刺史时,谢万坐着肩舆跑去挖苦:“人们都说您呆板,您果然是个呆子。”王述只能辩解说自己是“大器晚成”。
谢万写有《八贤论》,认为隐居远离官场比出仕更为高尚。
然而,当他的哥哥谢尚和谢奕相继去世,家族需要有人担当重任,谢安虽谦让弟弟,谢万最终还是接受了豫州刺史的职务。
到任后,谢万态度傲慢,时常妄自尊大。谢安劝他多和士兵接触,他却召集军官,挥手一掠,冷冷说道:“诸位皆是劲卒。”引得士兵们极度反感。
注:当时两晋社会,军人被严重轻视,谢万把军人称作“劲卒”,就像现代人称学生是“劳动力”那样,极具侮辱意味。
朝廷派他率军从中路援助洛阳,因东路主将荀羡因病退兵,他误认为北方燕军实力强大,竟然不战自退,导致军队溃散。士兵们一度想杀他泄愤,最后仍因谢安面子才放他离开。事后,谢万被废为庶人。
点评:谢万的问题何在?
(a)孙绰在与谢万关于《八贤论》的争论中指出,真正的高人是“心隐”,而非简单地隐居山林,不问世事才算高人。
(b)王羲之在谢万上任豫州刺史时曾点拨他:“君子应随事而行藏,礼贤下士,与部下同甘共苦,方能成就大业。”
真正的高尚情操,应是沉入琐碎繁杂的事务中,持之以恒地去经营,而谢万却如郗超所评:“把率性任性当作本事。”
换句话说,他把放纵任性误以为是才华的表现。
---
(2)王徽之的洒脱与执政风格
王徽之以雪夜访戴著称于世,他的洒脱多体现在社交场合,但这份洒脱用在官场和政务上,反倒令人不齿。
他在日常交际中言辞放肆,喜欢肆意评点他人:
曾见支道林脸上有些傲气,便嘲讽说:“要是胡子和头发都长齐了,岂不是更高傲?”令支道林尴尬不已。
他舅舅郗愔出任北府将军时,众人祝贺,他却反复在屋中念叨“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”,弄得舅舅全家尴尬万分。
前秦贵族苻宏逃亡至东晋,谢安设宴招待,苻宏霸气侧漏,众人不敢反驳。王徽之陪同,盯着苻宏半天冷言冷语:“他不过如此。”令苻宏难堪。
谢安看他“话多且浮躁”,颇不待见。
若说社交尚有率真之处,他在政务上的态度则令人失望:
桓温任命他为参军,王徽之整日披头散发,不理公务。后来桓冲继续聘用他,有一次问他负责哪个部门,他答:“大概管军马。”再问有多少马,他说“不知马,何由知数?”再问马匹死了多少,他说:“未知生,焉知死!”
一次随桓冲行军遇暴雨,王徽之从马上跳下爬进桓冲的车内,说:“公岂得独享一车!”桓冲承诺会提拔他,他却不以为意,挥手说:“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。”意指不愿阿谀奉承。
问题是,既然如此轻视官场,为何还要从政?
王徽之这种对政务的冷漠和轻蔑,在东晋官场极为普遍。像刘惔、王濛这些贵为王司马昱高参的人物,也多不理政务。
刘惔被讥讽为“居官无官事,处事无事心”。
何充作为难得的勤政官员,却被他们嘲弄讥讽。
反倒是那些不做事、善于摆架子的人获得清誉,成了时代的领袖;默默实干者反遭轻视。这样的风气,怎能成就大业?
---
在《晋书·殷仲堪传》中,我们看到上层士族的逍遥雅致,与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形成鲜明对比。
东晋时期,众多底层百姓多为北方流民,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痛,流落南方,却成为士族庄园的“僮奴”。他们或卖身为奴,或被掳为奴,更多的是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劳役,自愿依附于士族。
纵观中国历史,和平安定的朝代,广泛的百姓应该是“编户齐民”,享有基本人身自由。而东晋的广大百姓却多半处于半奴隶状态。
士族不仅毫无同情,反而对百姓施加压迫。以下两位名士的行为尤为明显:
(1)王廙,王敦的从弟,东晋著名书画家。
王敦排挤陶侃,安排王廙为荆州刺史。王廙上任后排斥陶侃旧部,滥杀无辜,贪暴成性,激起当地民众起义,荆州大乱。
王敦叛乱时,他不劝阻,反而助纣为虐。事后朝廷对他宽容有加。士族还称赞他“博古通今”,与谢鲲齐名。最终王廙安然善终。
若换做其他朝代,此时此刻早被满门抄斩了好几遍。
(2)殷浩之父殷羡,风流倜傥。
任豫章太守出京途中,地方士人写百余封托请信,他半路将信件投水,冷言:“沉者自沉,浮者自浮。”此语深邃却又冷酷。
但他本人在长沙为官时,贪残恶政,声名狼藉。朝中庾冰都难以提携其子殷浩。
唯有庾翼看得透彻:“上层士族为政多奸佞,弄出事端,终让下层寒士替罪。”
《晋书·良吏传》前言里,唐史家总结:两晋几无良吏,真正有德有才的寒士多被压制于下层,上层尽是高门大族子弟。
---
东晋士人与广大黎民都经历过五胡乱华的国破家亡苦难,且北方胡人政权始终是重大军事威胁。
因此,北伐成为东晋朝野的核心“政治任务”。
东晋虽被汉人视为正统,也有过多次北伐机会,但始终偏安一隅,忽视北方百姓的疾苦。
荀羡北伐时曾质问一名为前燕效力的汉族官僚:“你为何不以粮食款待我军,反助胡人为敌?你良心被狗吃了吗?”
对方答:“中原百姓受苦多年,你们都去了哪儿?”
东晋虽有多次北伐行动及预谋,如祖狄北伐、庾亮兄弟预谋、褚裒北伐、殷浩两次北伐、桓温三次北伐、谢安预谋北伐等,皆告失败。
原因多方面:北方形势复杂,指挥者无能,东晋内部不团结,互相牵制。
但更关键的是东晋高层普遍缺乏真诚的决心和团结精神,缺少励精图治的态度,只有谢安领导淝水之战一役成为例外。
---
作者:专栏《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》主讲人——徐华
更多精彩讲解,进入专栏观看
---
如果你需要,我还能帮你继续改写后续内容,或者针对某些段落再丰富细节。你觉得怎么样?
发布于:天津市正规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